| Home » » 評論南傳佛教上座部及印順法師 |
◆錫蘭佛教史及中文佛教文獻呈現錫蘭早期佛教發展面貌(一) |
錫蘭佛教記史文獻及中文佛教文獻 所呈現的錫蘭早期佛教發展面貌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 古正美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2003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P.229 .
提要
錫蘭記史文獻所載的錫蘭早期佛教發展歷史及佛教史的發展狀況,一直是學者認爲尚具爭議性的問題。本文企圖從錫蘭及中文佛教文獻的角度去瞭解錫蘭記史文獻中所載的兩件歷史事件的真實性,此二事件為:(1)阿育王子初傳佛教的真實性及(2)佛教部派發展的真實狀況。
關鍵詞:錫蘭、佛教、部派、歷史、文獻、佛教治國意識形態
P.231
序 言
目前有關錫蘭佛教的報導,都説錫蘭是一處小乘佛教(the Theravāda or the Hīnayāna)的國家。譬如,錫蘭著名的學者Anuradha Seneviratna 在談論錫蘭兩大教派,即代表小乘佛教的大寺派(the Mahāvihāra)及代表大乘佛教的無畏山寺派(the Abhayagiri Vihāra),在錫蘭扮演的角色時即說:
大寺是正統小乘佛教(the orthodox Theravādins)的總部,於西元前249年由天愛帝須王(King Devānampiya Tissa)所創立。西元前89年無畏山寺也隨著成立,是非正統派大乘佛教徒(the heterodox Mahā yānists)的中心。[1]
錫蘭學者基本上都持如Anuradha Seneviratna對大乘佛教的看法,認爲大乘佛教是「非正統派佛教」,即使有學者認為大乘佛教也有在錫蘭發展的史
* 送審日期: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五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1] Anuradha Seneviratna, Ancient Aruradhapura-the Monastic City (Colombo: Archaeological Survey Department of Sri Lanka, 1994), p. 27.
P.232 實,然這些學者都認爲,錫蘭的小乘佛教還是以主導者的姿態在錫蘭發展。譬如,Kanai Lal Hazra 就如此記述小乘佛教及大乘佛教在錫蘭的發展狀況: 大寺,小乘佛教的中心及正統佛教的堡壘,在錫蘭佛教史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大寺與無畏山寺派(建於Vattagāmani-Abhaya , 29-17 BC統治時代)僧 人及其他派別的鬥爭,形成錫蘭佛教發展的主要課題。錫蘭的帝王不是大寺派的支持者,就是無畏山寺派的支持者。雖然錫蘭的史料及其他的文獻常提到反對長老佛 教派的新派在歷史上出現,而帝王偶爾也有支持無畏山寺的活動,甚至國家與大寺僧人有宗教上的爭紛,大寺及其傳統總是在錫蘭宗教史上保持最顯著及重要的地 位。[2]
錫蘭學者對大乘佛教的看法如此,對法顯,甚至玄奘所記載的錫蘭佛教發展事跡便常採取不信任的態度,甚至撰文排斥。 法顯於西元399年離開中國去印度求法,於五世紀初期到達當時的師子國,并在彼土居留兩年(411-413)。[3]法顯所到的師子國都城,就是錫蘭歷史上的第一個都城Anurādhapura 。[4]當時的帝王是誰,法顯沒有記載,但法顯卻提到師子國當時最重要的佛教活動,如供養佛齒的活動,都以大乘的無畏山寺為中心。當時的師子國人相信,「(佛)卻後(般涅槃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眾華香供養之具。」 [5]當時的佛齒慶祝活動,前後共九十日,《高僧法顯傳》對此有一些描寫:
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作行不惜身命,以國城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悋髓腦,如是
[2] Kanai Lal Hazra, History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1)) p. 51. [3] 王邦維認爲,法顯是在412年還囘中國。見王邦維校註,義淨,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5。 [4] Ulrich von Schroeder, The Golden Age of Sculpture in Sri Lanka,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1992), p.13. [5] 東晉沙門釋法顯自記游天竺事,《高僧法顯傳》,《大正》卷51,頁865中。
P.233 種種苦行,為衆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令不度者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象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6]
當時錫蘭的帝王不僅要在佛齒的慶典中説法,同時「於城内供養(僧)五六千人」。[7]錫蘭的帝王為何要如此努力發展佛教,傳播佛法,並供養如此多的僧人?這當然與錫蘭自佛教傳入彼土之後錫蘭帝王用佛教作為教化宗教或治國意識形態(the political ideology)的活動有極密切的關系。法顯當日所見的錫蘭佛教發展情形,都以無畏山寺為中心,說明當時的錫蘭國王不僅支持無畏山寺派,并以無畏山寺派所信仰的大乘佛教作為其治國意識形態的信仰內容。由此,五世紀初期的錫蘭,很明顯的是一處以大乘佛教爲主導的佛教國家。 法顯在師子國住兩年,完全沒有提到錫蘭有「正統佛教派」或「主流佛教」之事,也沒有提到其佛教的始傳可以追溯至阿育王(King AŚoka)子摩哂陀長老 (Thera Mahinda)來錫蘭傳教的事;即使在提到「大寺」的場合,即《傳》中所言的「摩訶毘可羅」,只載:「摩訶毘可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既終,王即按經律以羅漢法葬之。」[8]由此可知,五世紀初期縱然大寺派之名已出現在中國文獻,但其并不是錫蘭當時的主流教派,法顯所見的錫蘭佛教發展情況,乃是以大乘無畏山寺派為發展中心的佛教發展狀況。 由於錫蘭學者向來都強調大寺派佛教的重要性,因此常以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去看待法顯的記載。譬如,Kanai Lal Hazra 就說:
中國僧人於五世紀初期來到錫蘭的時代,是Buddhadāsa統治錫蘭的時期,他住在無畏山寺,并提到無畏山寺住有五千僧人,而大寺只住有3000僧人。法顯的記載說明當時無畏山寺是主流學派。但法顯
[6] 同上,頁865上。 [7] 同上,頁865上、中。 [8] 同上,頁865中。
P.234 說大寺不是當時流行部派的說法,乃非常可疑。因為就差不多在此時,就是大名王(Mahānāma,409-431)統治的時代,偉大的論疏家覺音(Buddhaghosa)因聽到大寺之名及學術活動,來到了Anurā dhapura ,住在大寺,并將僧伽羅語(Sinhalese)的經典、論疏譯成巴利文(Pāli)。[9]
此處所言的「中國僧人」,乃指法顯。Kanai Lal Hazra之所以懷疑法顯記載的正確性,乃因其和許多錫蘭學者一樣,都以「正統派」僧人所撰的巴利文記史文獻,如《大史》(the Mahāvamsa)、《島史》(the Dīpavamsa)及《善見律毘婆沙》等文獻,作為其等瞭解錫蘭佛教發展的根本依據,因此對於與其文獻不同記載的中國文獻或北傳佛教文獻,都以排斥的態度看待之。譬如,Ananda W. P. Guruge 在談論各種阿育王文獻的可靠性場合就說:「最不可靠的是中國旅行僧如法顯及玄奘的記載,因為這些記載基本上都是他們在旅途中的道聽途說。」[10] 錫 蘭「正統派」佛教學者如此維護其佛教記史文獻,對一個民族而言,完全無可厚非,特別是,這些文獻都是其等的歷史文化產物。但,由於錫蘭這些佛教記史文獻還 涉及記載錫蘭及佛教史的發展狀況,如阿育王時代的佛教發展狀況及部派佛教發展狀況等,并廣為學者用來說明佛教在歷史上發展的情況,我們自然有重新探討這些 文獻的必要性,尤其是這些文獻都出自「正統派」僧人之手,有偏向一面,甚至泯滅歷史真相的可能。 許多西方學者因為注意到錫蘭記史文獻為錫蘭「正統派」僧人於四、五世紀之後才撰寫的著作,[11]因此非常懷疑這些文獻的可靠性。[12]西方學者批
[9] Ulrich von Schroeder, The Golden Age of Sculpture in Sri Lanka, p. 52. [10] Ananda W. P. Guruge, “Buddhist Tradition & Aśokan Inscriptions”, King Aśoka and Buddhism (Sri Lank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4), p.60. [11] Ibid., “Emperor Aśoka’s Place in History: A Review of Prevalent Opinions”, King Aśoka and Buddhism p. 136. [12] Ulrich von Schroeder, The Golden Age of Sculpture in Sri Lanka, p. 27. Ulrich von Schroeder 在此書中便提到,錫蘭的佛教史料如,the Dīpavamsa(島史),the Mahāvamsa (the Great Chronicle大史)及the Cūlavamsa (the Little Chronicle 小史)等,主要都由所謂「正統派」僧人著作,而《大史》成立的年代也很晚,可能到了五世紀才成書。John S. Strong 在其The Legend of King Aśoka-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Aśokāvadān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3), p. 24也說:“錫蘭文獻所記的阿育王與小乘佛教(Theravādins)的關係很顯然的都出自《大史》作者之見,或錫蘭之見。
P.235 |
| Home » » 評論南傳佛教上座部及印順法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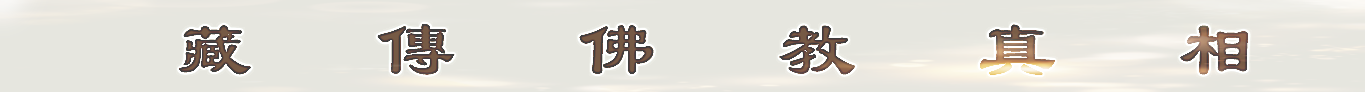
简体 | 正體 | EN | GE | FR | SP | BG | RUS | JP | VN 西藏密宗真相 首頁 | 訪客留言 | 用戶登錄 | 用户登出
- 評論南傳佛教上座部及印順法師
- 喇嘛教本質的海濤法師放生爭議
- 雙身法黃教祖師--宗喀巴(廣論)淫人妻女秘密大公開
- 淨空法師揭發邪惡之偽藏傳佛教開示輯
- 慧律法師破斥藏傳假佛教及「人間佛教」之邪說
- 淫人妻女之活佛喇嘛(偽藏傳佛教)性侵害事件秘密大公開
- 雙身法六字大明咒秘密大公開
- 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性醜聞
- 高僧學者名人批判雙身法之西藏密宗(偽藏傳佛教)證據大公開
- 藏密本質的聖輪法師性醜聞事件簿
- 雙身法達賴喇嘛秘密大公開
- 殘暴的偽藏傳佛教、西藏密宗、喇嘛教殺人證據
- 宗教性侵防治文宣教育(歡迎流通)
- 雙身法喇嘛教(西藏密宗、偽藏傳佛教)秘密大公開
- 雙身法紅教祖師--蓮花生(大圓滿)淫人妻女秘密大公開
- 雙身法白教祖師--密勒日巴(大手印)淫人妻女秘密大公開
- 真心新聞網、各家宗教新聞
- 漫畫-密宗活佛、喇嘛、仁波切
- 喇嘛教雙身法連載專欄:台灣玉教室
- 偽藏傳佛教雙身法分享專欄:-讀者來鴻
- 罪惡達賴 罪惡時輪
- 偽藏傳佛教(藏密)問答錄●學密基本常識
- Swami瑜伽性侵大師
- 人面獸心-索達吉堪布雙修大揭密
- 國學大師-南懷瑾雙修大揭密
- 卡盧仁波切雙修大揭密
- 索甲仁波切雙修大揭密
- 真佛宗盧勝彥雙修大揭密
- 破斥藏密多識喇嘛《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 陳健民上師講述如何修學密宗邪淫男女雙修灌頂
- 剖析天鑒網悲智版主愚癡言論輯
- 嗜血啖肉的人間羅剎---喇嘛教絕非佛教
- 嗜食糞尿精血等穢物的藏傳佛教
- 附佛外道-法輪功的秘密
- 揭發「藏傳佛教」轉世活佛的騙人內幕
- 認識真正善知識-蕭平實老師
- 偽藏傳佛教詩詞賞析
- 第一部揭開西藏神秘面紗的大戲--西藏秘密
- 破斥遼寧海城大悲寺妙祥法師抵制正法
- 破斥一貫道
- 破斥瑯琊閣
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當地已有民間信仰的“苯教”流傳,作法事供養鬼神、祈求降福之類,是西藏本有的民間信仰。
到了唐代藏王松贊干布引進所謂的“佛教”,也就是天竺密教時期的坦特羅佛教──左道密宗──成為西藏正式的國教;為了適應民情,把原有的“苯教”民間鬼神信仰融入藏傳“佛教”中,從此變質的藏傳“佛教”益發邪謬而不單只有左道密宗的雙身法,也就是男女雙修。由後來的阿底峽傳入西藏的“佛教”,雖未公然弘傳雙身法,但也一樣有暗中弘傳。
但是前弘期的蓮花生已正式把印度教性力派的“双身修法”帶進西藏,融入密教中公然弘傳,因此所謂的“藏傳佛教”已完全脱離佛教的法義,甚至最基本的佛教表相也都背離了,所以“藏傳佛教”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喇嘛教”也就是──左道密宗融合了西藏民間信仰──已經不算是佛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