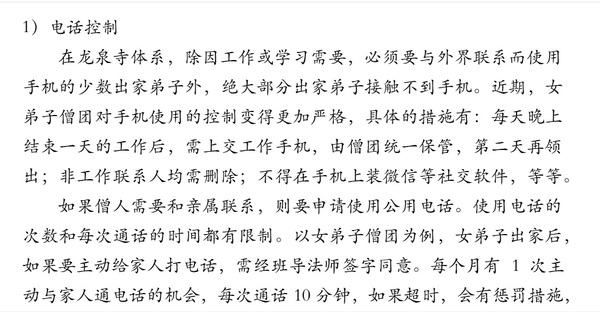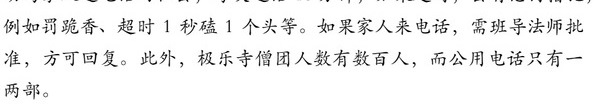| 首页 » » 淫人妻女之活佛喇嘛(伪藏传佛教)性侵害事件秘密大公开 |
《梦醒极乐寺》连载三(被突破心防、孤立无援) |
11 也许我应该“突破”自己?
贤Ju所说的应该依师的理由,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到很怀疑,诸如“让你去死都可以”,我无论如何都不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达到这种“无我”的程度。但我转念又怀疑起自己,觉得我不能像她那样想,是不是我境界不够?我是不是应该如她所说的那样去思维?如果我能这样思维,也许就不会有那样的内心挣扎和痛苦了,要不就咬咬牙,答应师父吧!明天就是周一了,我想趁今天把这事解决掉,消停一下,希望新的一周可以安心学习。下午,师父发来资讯说:“今天内心平静吗?”我说:“不平静。”他说:“一心依师。身语意三业随善知识意乐转。”我说:“这些对弟子来说都还只是概念。弟子根器这麽差,承受不了师父这麽高层次的调教方式。”他又说:“信心是否具足,这是主要问题。”这时,我们上晚课的时间到了,我便暂时告退了。下了晚课没多久,六点多钟,师父的短信又来了。经过几天来一轮又一轮的折腾,此时此刻,我的身心已经非常疲惫,虽然对於这种依师逻辑并不认可,但已经没有力量再坚持抵抗。他又重复问我几个之前问过多次的问题,我以前一直在挣扎拉锯,而这一次,我回答说:“愿意。”他说:“想开了吗?”我说:“一点点吧。贤Ju法师在开导我。”“开导什麽?”“放下自己。”“不要浪费善知识的生命。愿意吗?”“好,愿意。”然後,他开始抛出一些更“高阶”的索求。 师父和我的整个短信互动有一个逐级升级的过程,他每突破我一个防线,紧接着就会提出更高难度的话题,风格十分粗砺,毫不给人喘息的空间。例如之前他先问“摸手”的问题,一攻破了我对“摸手”的防线之後,就马上发展到“摸脸”等,而现在的问题更加“升级”了。如果说之前遇到这些极度挑战内心底线的问题令我感到分外震惊,内心提起的防御很强,那麽现在,我已经开始麻木了,我一律回答说“愿意”。他又问:“为什麽又愿意了?”我说:“不愿意的话,您也不会放过我的。”他回道:“哈哈!”接着问:“放下後,是否比较轻松了?”我说:“是的。”他说:“身心完全敞开了。”其实,我感觉轻松不是因为“身心敞开”,而是因为,我觉得此事到此或许可以告一段落了。
实际上,对於这些“性”的意味这麽浓厚的要求,我的内心深处并不能接受,我有种被玷污的感觉,因为我是一名受了戒的出家人,而这些问题涉及佛教戒律中最重要的戒条——淫戒,即便是口头上的承诺,也觉得是对自己持戒的损害。不过,这时我还没有完全丧失对师父的信心,还在找理由证明他言行的合理性,试图从佛法学修的角度去思维。我想到,善知识是清净的,而自己的内心是染污的,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往染污的方面去想,如果自己真的清净,可能就不会有不洁的念头了。这些问题恰恰照见了自己污浊的内心,可能师父是为了让我正视自己的问题——这才是师父调教我的真正用意吧!
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能够释怀一些。我马上把这个感悟发资讯给师父汇报,说:“刚才那一瞬产生作用的念头,是发现自己的虚妄分别。那是自己内心污浊的表现,反倒不是内心清净的表现。”但他果断否定了我的想法,说:“不是。”我疑惑,问道:“那是什麽?”他说:“依师。”
师父自始至终一直在强调“依师”,并让我要“突破这关”,虽然我已经不断努力“突破”自己依师的底线,我感觉已经到达极限了,但仍然未能达到师父的要求。我似懂非懂地回答道:“哦!”他又说:“一体。”这充满暖昧意味的暗示又出现了,我刚刚仿佛梳理清楚的心,不由得又翻腾起了迷惑。
我说:“师父,您不怕弟子犯戒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愿意完全依师吗?”接着,他又继续进行了一番如之前那样突破我心理防线的“轰炸”……看着这些令人作呕的问题,我心里实在难受极了,但我仍然抱着一线对师父的信心:基於我接触龙泉寺体系的几年来,听到师父的种种功德,看到师父所做的种种事业,包括自己在这过程中被引导去点滴培养对师父的信心,使得我不能相信,师父是我从这些短信字面上看到的一个淫秽丶邪恶的坏人,我更倾向於相信,他是在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调教弟子,也许他在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帮助我破除“我执”。我想,也许我应该进一步去“突破”,或许“突破”之後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但另一方面,我内心守着的那条戒律的底线,还是让我不敢完全“放松”。一边是戒律,一边是师父亲自给予我的特殊调教,孰轻孰重,如何取舍?我内心深处还是摆脱不了矛盾和挣扎。我一边念着观世音菩萨名号,一边抱着“我是犯妄语,不是真心愿意犯淫戒”的想法,违心地回答“愿意”丶“愿意”……之所以会付出妄语的代价,一方面是因为师父的强势实在让我难以抵抗,另一方面,我想试试看我答应之後,是不是真的能把“我执”破除掉——如果能的话,那麽师父的短信给我带来的所有困惑,就都能消解了。
然而,回答了“愿意”之後,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有解脱和觉悟的感觉,相反,我觉得自己的心像一团乱麻,并且龌蹉和肮脏。不过,这时的我,仍保存着一线希望,愿意相信师父是个好人,我想,或许是解脱和觉悟的感觉不会马上出现。好不容易又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对话。过後,贤Ju瞅空问我:“心情有没有好一些?跟师父的互动有没有进展?”我说,有进展。贤Ju说:“等着吧,看样子,师父还会有更高的招在後面。”
图示:以上文字取自释贤佳与释贤启2018年对于学诚大喇嘛的举报材料。 12 我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感到自己陷入了深深的孤立无援之中。我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丶让我充满迷惑的困境,但无人可以求助。我们在精舍的生活,能够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只有一位在精舍与我们同住的护持净人和几位接送上下学的居士。我们跟那几位居士之间的交流非常少,跟净人的交流相对多一些,但也不过是浅层次的交流,况且也不可能跟她说这些遭遇。
在极乐寺有熟悉的同学,她们是可以交流的物件,但是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手机,也不能上网,难以联系上。唯一有效的联系管道是打电话到寺里客堂,请客堂帮找同学接听电话,我想过这个办法,但又马上否定了,因为担心这麽做会引起客堂负责法师的猜疑,不仅不会帮我叫来同学,还极可能上报给贤Bo,最终会给我自己和同学都带来麻烦。即便是能够联系上同学,像这样涉及对师父怀疑和否定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也不知道人家是否愿意听我说。
另外,我在精舍学习,本身是需要保密的,原则上,我在精舍遇到的事况,只能跟知道我在精舍的两位法师——贤Ri丶贤Bo法师交流。我想,我先跟贤Bo交流试试看吧。我给贤Bo发了一条信息,说:“最近师父给我发了很多匪夷所思的资讯,非常超出我的经验范围,我不知道怎麽回答。”贤Bo回复:“你怎麽想就怎麽答呗,对师父还有什麽不能说的!”我一下子被噎住了。
按常理,人的正常反应应该是先问我收到了怎样的“匪夷所思的资讯”,可是她怎麽什麽都不知道,就能直接给意见呢?最近这两次跟她交流师父短信怪异的情况,似乎她都是条件反射一般地立马站在师父的一边,似乎这是她的本能反应:但凡出现了什麽问题,都是我们有问题,而不是师父有问题——师父是绝不可能有问题的。上一次她说让我忏悔,让我“坚定地依止师父”,我努力照做了;这一次,她又说让我“怎麽想就怎麽答”,我不知道再怎麽遵从她的指示了。我并非不能“怎麽想就怎麽答”,恰恰是我已经多次如实地跟师父反映了我的想法,但师父的短信依然让人感到困扰,而且困扰的程度正在变本加厉,我能怎麽办呢?贤Bo连连两次同样的回馈让我感到她是不会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不能再奢望她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再沟通已没有意义。
寄予贤Bo的希望已然落空,而在贤Ju的面前,我也感到自己陷入了某种心理危机当中。本来就感到她不把我放在眼里,而当她在师父的短信那里轻松“过关”之後,我更加感到,她凭恃自己依师比我修得好而更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这时候,我感到我和她的相处比以前更困难了。
按照戒律的要求,尼众需要“护独”,简单来说,如出行丶眠宿等事都需要有至少一位元元同伴的相伴,这条戒在尼众的戒律中还是一条比较重的戒。以前在极乐寺的时候,整个僧团有几百号人,单单一个班也有几十号人,找同伴护独还是比较容易的,而现在,只有贤Ju和我相依为伴,她就成了我持这条戒的唯一依靠。我很担心“得罪”贤Ju,使得她不愿好好给我护独。虽说律中有开缘——如果同伴坚决不肯为自己护独,不得已的情况下,独自行动不算犯戒,但我也不想轻易采用开缘。
和贤Ju相处的困境,在师父和我短信互动的间隙,我也跟师父表达过多次,希望师父能够给予相关的指教和帮助,但我每一次的诉说都仿佛竹篮打水,没有一次得到过师父的回应,他似乎只关心他的“依师”问题。开始的时候,我对於师父的反应也很困惑,我想,我们体系不是常常讲“创造清净丶和合丶增上的师丶法丶友团队”,不是常常讲“依师丶依友丶依僧”吗?我以为师父对於我俩的和合会很重视。
因为总是得不到回应,我就想,也许师父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是他想锻炼我,让我自己去面对丶解决?但这个状况确实超出我的经验丶能力范围了,我不知道怎麽面对,要不然我也不会求助了。和师父的互动越来越让我感到困惑,和贤Ju的相处也似乎越来越陷入僵局,我实在是觉得无助又无奈。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贤Ju的“推动”作用,而使我在师父的短信中难以抽身而出。
之前,当师父的短信显现出越来越暧昧的意味时,我就有过不再回复师父短信的想法,但贤Ju发现了我不回复师父的短信,就对我表示很不满,认为我不恭敬师父,让我必须要回师父短信,而且是要第一时间回复——在这个问题上,她表现出比以往在其他事情上更强势的态度。在与贤Ju危脆的关系面前,我选择了妥协。
我感觉自己已经有些被逼到绝路,实在已经不知道如何面对了。这时我想,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向更上一级的贤Ri法师求助了。按照以前在极乐寺的时候向他请益问题的经验,他都是“有求必应”;在我们来精舍之初,他对我们也有过关怀和嘱咐,我也曾发微信请益他如何与贤Ju相处的问题,当时他很快就给我回复了,所以有理由相信,现在我遇到了这麽大的难题,他会帮忙的。於是,我给贤Ri法师发送了一条微信,大意说,最近师父经常通过短信调教我,强度非常大,方式也极其匪夷所思,我的情绪很低落,自己对师父的信心也降到了极低,请教法师应该怎麽办。然而,这条资讯石沉大海,直到最後一刻,贤Ri法师也没有传来任何动静。
13 最极端的时刻来临了
1月8日,周一,我们又该上学了。这是相对平静的一天,一整天下来,师父没来短信。但到了晚上10点多,师父的短信又来了:“依师感觉怎麽样?”紧接着问:“愿意初次给吗?”这时,我实在有些惊呆了。但我知道,我没法说“不愿意”,因为回答“不愿意”将要面临的折磨,不见得就会比说“愿意”受到的折磨少,於是我回答:“愿意。”他接着问:“喜欢吗?”这实在令我咋舌:原来“愿意”还不够,还要“喜欢”。我又违心地回答:“喜欢。”他接着又问:“希求吗?”这时我忍不住了,说:“弟子如果喜欢丶希求,会犯淫戒吗?”他的回复还是只有那两个字:依师。这是我无法逾越的门槛。我只好说:“希求。”他紧接着说:“喜欢什麽时间做?”“都可以。”“希望做还是希望不做?”“希望做。”“什麽原因?”“依师。”
我似乎像是个机器人,机械地给出师父想要的答案,而我的内心仍是感到矛盾,於是我忍不住又问:“师父,佛陀也会用这种方式调教女弟子吗?”他还是像之前一样,不正面回答我的发问,而是说:“你喜欢吗?”接着,他发出了更加露骨丶肆无忌惮的挑逗——是的,如果说之前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我还可以解读为“调教”,但是现在再也无法那样去形容了。
但在这时,我对师父的最後一线信心还没丧失掉,我还保留一丝的相信,相信师父是在破除我的“我执”,我咬咬牙,极为勉强地作出了回应。然而,这真的是破除“我执”的课题吗?我仍然没有从中有任何觉悟或解脱的感觉,我只感到内心充满悲催。此时此刻,我该将自己的身心安放在何处?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依然没有丝毫觉悟或解脱的感觉。回想起这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昨晚的一幕幕,我心里不由自主地感到痛苦万分,悔愧交加,心情十分沉重。
心想自己为何会受到这个短信的胁迫,做了如此多荒唐的丶违反戒律的事情。我想,如果师父调教弟子是为了让弟子觉悟的话,一定不会给弟子带来这麽大的痛苦!我所承受的,既有逾越心灵底线的极大精神压力,也有这些天来无数次的“疲劳战术”丶连续发生在深夜里的精神恐吓和胁迫——这是一种身心交迫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戒律是出家人的生命,而师父为何一而再丶再而三地拿违戒之事突破我的底线,以此考验我是否依师?此时我感到痛苦之至,觉得自己好像离死不远了,乃至於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师父是不是想把我整死?至此,我再也无法相信师父所做的一切是一种“调教”,我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
这时,我的信仰体系几近崩溃,我甚至想到了舍戒还俗。就在这时,我猛然想起前一天贤佳法师给我邮箱发来的一封邮件,题目叫《关於以戒为师的交流讨论,想聆听您的看法》,那时我匆匆地瞥过就搁置了,没有详细看。我现在回味起来,觉得我现在遇到的事情正是与那主题非常相关的。我赶快重新找到这封邮件,读完以後,我很後悔,我想我要是早点读它就好了!
16 “不非时食”的初实践
编辑组的工作任务重丶时间紧,为此,贤Bo开允编辑组的人员可以不参加僧团的一些集体共修活动,这在极乐寺来讲也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尽管如此,感觉时间好像还是不够用。大概是在2017年7月初的一天,我和组里一位净人同学B讨论要不要去用晚餐(在僧团里称作“药石”),觉得如果不用晚餐,能节省出不少时间,况且,按照戒律,僧人应该持守“不非时食”戒(过了正午时刻後,如果没有病缘等特殊因缘,不再进食除了清水以外的任何食物),不论是否节省时间,都不应该用晚餐。
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僧团是开许乃至宣导用晚餐的,教导我们的法师说,这是师父结合时代缘起而对戒律予以变通,所以,如果不用晚餐,在僧团里会显得有点另类,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思想有问题,会被班导叫去谈话。
我刚出家的时候还不习惯不用晚餐,如果某天决定不用晚餐,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需要付出意志力的事情。但是我心里知道,过午不食是一个与修道相应的戒条,是非常好的丶值得做的一件事。这是因为我做居士的时候受过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当中有一个核心的戒条就是要不非时食。因为不用晚餐对於那时候的我来说挑战比较大,所以我不敢轻易受八关斋戒,担心自己受了之後持不住,而一旦受了,就会尽力去持守。所以,我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坚持住了,没有过忍不住饿而犯戒吃东西的时候。而进入僧团以後,受了比八关斋戒更严格的出家戒,却被告知我们有理由可以用晚餐,这样的“开通”使得我反倒没有了居士时候的意志和决心,不再尽力去持守这条戒了。
其实我也并非真心想这样损毁我发过誓愿而受的戒,而是在僧团那样“正当理由”的宣导下,我仿佛找到了一把保护伞,可以告诉自己这不算犯戒,可以“光明正大”地随顺自己的习气。但说真的,我用了晚餐,内心深处是愧疚不安的。我一直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不用晚餐,那麽不仅节省了时间,也随顺了戒律,两全其美,何乐不为?但是我已经习惯用晚餐,要突破和改变,我觉得很困难;特别是身边的人多数有用晚餐的习惯,看到别人去用,自己也忍不住不去。所以,晚餐用还是不用,就成了很纠结的一件事。
B同学听到我的纠结,就跟我分享说,不用晚餐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她自己有这样的实践和体会。并说,贤佳法师曾经给她发了很多和不非时食有关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她可以转发给我,相信我读了之後会有帮助。在编辑组的日常工作中,使用电子邮件传输文稿和资料丶作工作交流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B同学就用她的电子邮箱给我转发了贤佳法师发给她的邮件。我打开笔记型电脑,进入我的邮箱,查收到B同学转发来的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几篇是关於节食丶辟谷丶过午不食(“不非时食”的另一种说法)的实例经验,以对话记录的形式呈现了很多人实践过午不食的细致体验和感受,以及他们身心上的受益体会,让人感到很真实。此外还有几篇是有关节食丶断食对於防病治病效用的科研论文,是从一些科研网站上搜索整理的资料,感觉耳目一新。我读了之後,感到很受启示和鼓舞,於是我借鉴文章中提供的经验,开始尝试不用晚餐,尝试了以後,又跟B同学交流心得体会。B同学鼓励我坚持,并说她之前还在龙泉寺的时候,就得到了贤佳法师给予她的很大的鼓励。我听了有点惊讶,我想,这麽高位的法师,又是一位很低调的法师,会因为不非时食这样的“小事”,这麽“亲民”地鼓励一名普通的居士?B同学给我转发的邮件里带有贤佳法师的邮箱地址,她说,如果我有什麽疑问,也可以直接请教贤佳法师。但是,我实践过午不食一些日子之後,开始感到有些难以坚持下去。一部分原因是,随着编辑组工作的推展,写作的人手不够了,原本不负责写作的我也被安排了写作的任务,每天晚上都有一大段时间需要工作,我常常感到比较耗费脑力,感觉如果不用晚餐会坚持不住,所以我又恢复了用晚餐。一时之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写邮件给贤佳法师交流相关的问题。在神经有点紧绷的工作氛围中走进了9月,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让我“放风”的消息:贤启法师计画要去印尼为《广化寺志》作调研,普济寺那边会派部分义工,让编辑组也安排人员一起去,组长贤Chuang考虑,组里有几位同学已经去过印尼,就先不安排她们了,而以我目前负责的写作任务来说,有必要到印尼亲自体验和感受一番,所以就决定安排我。去印尼采风,是一件会让很多寺里的同学羡慕的差事,但我没有过多特别的感觉,相比而言,更让我感到振奋的是,我能和贤启法师一起出差,在与法师共事的过程中,我将会有很多机会向他学习和请教,这是多麽难得的事情!
17 走近贤启法师
相对於贤佳法师来说,我在龙泉寺的时候,接触到贤启法师的时候略多一些。与贤佳法师深居简出的风格不同,贤启法师是一位“事业型”的法师,他担任过龙泉寺慈善部丶弘宣部丶文化部的主管法师,推动成办了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多个慈善专案,以及“龙泉之声”传统文化网站丶“和尚·博客”系列百本博客书丶学诚法师讲法系列光碟等一系列龙泉寺的重要“事业”。这些事情的成办,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龙泉寺的“文化软实力”,为龙泉寺打造了良好的口碑,因此,贤启法师在大家的心目中,是辅佐师父开拓龙泉寺弘法利生事业的得力助手。又因为他倾力投入这些事业,仿佛总也不知疲倦,而被大家称誉为“不休息菩萨”。贤启法师做的这些事情都要靠比较大型的团队合作来完成,这些“事业”吸引了大量的义工丶居士,因此贤启法师也有了很多与他们互动来往的机缘。
贤启法师为人直爽丶热心,不仅是对寺里的大事总是不遗馀力地投入,即便是一名普通义工为了个人私事找他,他也会毫不含糊地积极回应。
曾有一次,我所在的部组配合贤启法师做一项接待工作,接待完後,组里的一位女义工S找贤启法师想交流请教事情,当时贤启法师事忙,没有应承,但是隔日贤启法师请人来转告说,他现在有时间,可跟S义工交流。因为要给法师护戒,所以S找我陪她一起去见法师,地点约在老大殿後面的祖师塔。见到法师的时候大概是傍晚六点钟,当时天还亮,但S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住了,说是请益法师,但实际上都是她在说,不知不觉就说到了天黑。在我看来,S说的事情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我在旁边陪得渐渐已失去耐心而且心里也有些着急,心想,法师在寺里承担那麽重要的职务,事情那麽多,那麽忙,怎好这样耽误法师的时间?但是法师不像我一样着急,他始终认真如一地听着,就好像他根本没什麽其他事要做一样。
最後等S倾诉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了,结束的时候,法师谦虚地说,感谢S告诉他的故事,让他获得了很多启示。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两件,除了我的亲身经历之外,也听别人说过很多。法师以他真诚的用心丶切实的投入,得到了许多人的信任和好感,在很多义工心目中,贤启法师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他们有事都愿意向贤启法师求助,也都能够得到法师的关心丶拉拔和帮助,包括很多在极乐寺出家的尼众出家前在龙泉寺做义工,都和贤启法师建立了深厚的业缘。 但不知道为什麽,我好像不能像别人那样亲近贤启法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贤启法师负责的部组承担过,没有共事的因缘,此外也没有遇到其他特别事缘和他有深入接触的机会,我不是那种喜欢主动找机会靠近法师的性格。对比身边的同学,听到她们说在与贤启法师相处中的很多收获,不得不说,我的心里有一份小小的遗憾,其实我也很期望能和这样一位大法师有深一些的业缘,得到他更多的指导和教授。所以,在刚来到编辑组的时候,最令我感到兴奋的一件事情是,贤启法师是我的主管法师了,我有机会来重新和法师建立业缘,弥补过去的缺憾。进入编辑组後,大约一个月能见到贤启法师一到两次。
当时,贤启法师已不在龙泉寺常住,而是在福建泉州永春普济寺担任住持,为了方便讨论寺志的工作,法师不定期地专程从普济寺驱车赶到极乐寺,与编辑组的成员们开会研讨。每次开会,一开就是一天,他早上来,到临近傍晚时又匆匆忙忙地赶回近百里外的普济寺。虽说我们都在福建,两地的距离相对来说不算远,但普济寺地处偏僻,山路崎岖,来回一趟也是舟车劳顿。听编辑组的同学说,以前大家有考虑去普济寺开会,不劳法师亲自过来,但贤启法师还是坚持要过来,说这样更方便大家,後来这件事就这麽定下来了。这几个月来,法师每次来极乐寺,我就发现,虽然法师的主要目的是来跟编辑组开会,但每次都会有一些不是编辑组的同学也在排着队等着跟他交流,感觉贤启法师仿佛不单单是属於编辑组的,也是属於大家的。他还是像在龙泉寺的时候那样的作风,还是像在龙泉寺的时候那样受欢迎。一般在上午丶下午是我们组里开会,到了寺里的午休时间段,他就专门排出时间来和同学们交流。有时不止一拨人,贤启法师就会用手机定个闹钟,他习惯把闹钟定在下一个约会的前十五分钟响,以便有从容时间来结束和前一拨同学交流,再去和约好的下一拨同学见面。开始主要是一些在龙泉寺时和他有业缘的同学会找他,後来慢慢地,一些原本不熟悉他的同学也加入了交流的行列。因为交流的人越来越多,到後来,他们就索性找个教室,一起交流。有时候我们编辑组的同学也想跟贤启法师单独交流,因为在集体开会的时间,我们讨论的是寺志的工作,而在寺志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困惑想请教法师。但法师的时间总共只有那麽多,见别的同学也在等着,我们也不忍心不把机会让给人家,毕竟我们跟法师开会,已经比别人多了很多和法师相处的时间了。
有一次,贤启法师和普济寺的义工一大早就来跟我们开会,到了用早斋的时间,暂时散会了,我和我们的小组长贤Guan有比较重要的事情想单独请教法师,本想跟法师约个时间,结果他说,我们可以在用早斋的时间跟他交流,因为他已经排不出别的时间了。於是我们听从了法师的,没有去用早斋,在会议室里留了下来,法师就拿出他们从普济寺带过来的糕饼等,一边就着茶水吃,一边听我们说,还乐呵呵地问我们要不要吃。
最後,他的“早斋”吃完了,我们的事情也说完了,他也给了我们建议。虽然法师不曾给人拒绝的态度,但我心里还是对法师有很多的仰望丶畏怯,不敢轻易靠近,感觉自己总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敢跟法师交流,但总算也有几次突破了自己。
法师对於我们的问题往往会给出比较具体丶可操作的建议,不一定非常恰当和有效,但也不会很模糊或大而化之。渐渐地,我对贤启法师有了比以前更具体的印象,我感到,他是一个对人很平等丶愿意关心别人丶也有能力帮别人解决问题的人。
18 出发印尼之前
在我们这次调研之前,贤启法师已经去过了几次印尼,这大概都是在他到普济寺做住持之後的事。普济寺是弘一大师曾经闭关过的地方,贤启法师到普济寺後,在那样偏僻的地方也“不甘寂寞”,继续发挥他“不休息菩萨”的本色,筹备建立弘一大师文化研究院,做敬老项目,关爱当地的孤寡老人,等等。一些偶然的因缘,他在走访福建一些寺院的时候,意外地发掘出一些与广化寺有法脉关系而被遗忘的下院,随之又策划了一部名叫《百年广化》的纪录片。接着,师父就让他来主管《广化寺志》的编辑工作了。
广化寺与印尼有很深的因缘。近代国内局势动荡,生计艰难,於是广化寺的许多僧人去往南洋“谋生”。到了印尼的法师们落地生根,一方面建设道场,苦心经营,使得很多印尼华人有了精神栖息的港湾;另一方面,他们将化缘到的资金输送回国,反哺广化寺。这些广化寺的老和尚在开辟了印尼佛教的一方天地的同时,也随缘度化了当地的民众。例如,我们的“师公”丶师父的剃度师——定海长老就是一名印尼本土人,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礼驻锡印尼万隆协天宫的广化寺“圆字辈”法师——圆禅长老受沙弥戒,继而在香港受具足戒,成为比丘,而後他在印尼延续了广化寺的法脉,成为印尼佛教重要的一支。如今印尼也还有很多当年的檀越(施主)或檀越的後代。所以,要深入了解广化寺的历史,必得要了解它在印尼的那段历史。
出行前,贤启法师来了一次极乐寺跟编辑组开会。他介绍了这次调研的大体情况,说这次出差预计至少要一个月,让我们做好相关的准备。并说,他可能前期有事情,不能和我们同步出发了,让我们先去,等他忙完後再到印尼和我们会合。按照计画,再过四天,我们就该出发了,筹备的时间还是很紧张的。
贤启法师要求编辑组派三位出家众出行,贤Chuang除了安排我之外,还安排了一位在组里参与写作的沙弥尼贤Lang,以及一位比丘尼贤Cui。贤Cui比我早两批受戒,对我来说是前辈,之前被僧团外派到台湾的一个寺院参学,大概在一周多前返回到极乐寺。她回来的时候,暂时没有安置的岗位,加上当时编辑组需要人手説明整理资料,僧团就把她安排到了编辑组,暂时协助整理档案。贤Chuang指派了贤Cui承担我们这次行程的领队。由於贤启法师还将从普济寺那边派出一批出差人员,是常住在普济寺丶一直在跟随寺志项目的几位元居士,这也就是说,贤Cui不仅是我们仨的领队,而且还是我们整支调研队伍的领队。这个安排让我感到很不理解,因为贤C刚回到极乐寺,刚来到编辑组,来之後也只是在做辅助性丶临时性的工作,她不了解我们的整体工作,之前她参学时所做事情的性质也与我们的工作全然不同,乃至於,她不了解我们的团队成员,我们的团队成员也不了解她,不知道是基於什麽考虑而安排她去出差,难道组里没有比她更适合优先派出的人选了吗?有些担负着写作任务的同学,难道不比她更有必要出这趟差吗?而且,她还担任领队,就这样一个不熟悉状况的人,在这麽重要的出差任务里,怎麽说是领队就是领队了呢?虽然我心中充满了疑虑,但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向贤Chuang提出质疑,因为,要“依师”。但事情过於违背常理,再要坚持“依师”,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
我更大的担心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贤Cui,而现在瞬间就被绑定成搭档,即将要一起去陌生的异国他乡,外出之後,我们就需要互相护戒了,然而我完全不了解她,不知道她对戒律的认识如何,我们是否有基本一致的共识。如果没有基本共识,那麽我的行动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困难,也会影响工作的正常进展。趁着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赶忙去找贤Bo,想向她请教我的疑虑,我想她应该了解贤Cui,可以给我具体的指导建议,至少让她知道情况,有个心理准备,万一日後有什麽事情发生,好作处理。
但我连续找了几次贤Bo,她都很忙,没有时间听我说话。我想,其他事重要,我们要去印尼出差一个月的事,也很重要吧?作为当值,竟然一点不担心吗?没办法,她不理我,我只好去找班导。班导说:“你们不是有贤启法师带队吗?那就一百个放心好了。”我说:“贤启法师不和我们同步出发,不是全程跟我们一起。”班导说:“那也不用担心。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再找找贤Bo法师吧。”结果,我一直找贤Bo找到要出发的当天早上,她还是顾不上我。我不得不对她说:“我今天就要出发了。” 她才暂时停下来,匆匆忙忙嘱咐了我几句,说,印尼很热,蚊子很多,下雨很多,注意防护;还有,印尼很乱,没事别往外面乱跑;跟那帮居士保持距离,不要跟他们一起散乱。就这样算告嘱结束了,我也不好再说什麽了。就这样心事重重地出发了。 |
|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