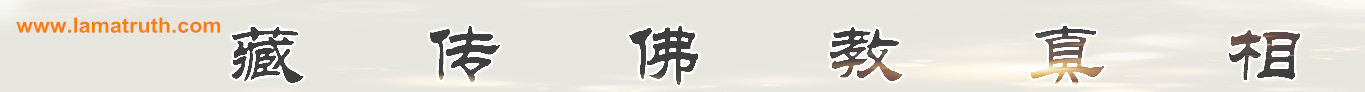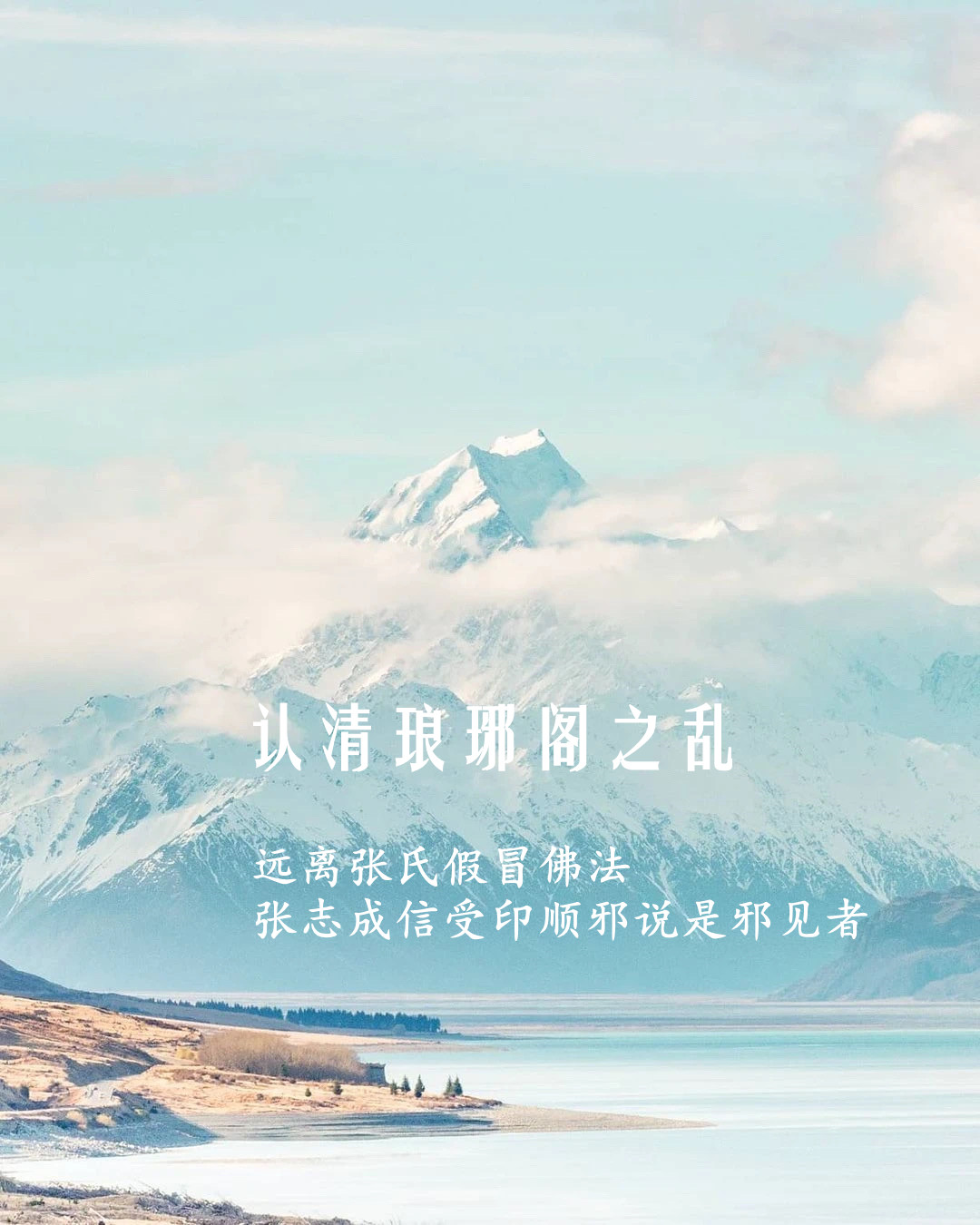| 首页 » » 破斥琅琊阁 |
与张志成先生聊聊16 | 空谷跫音——护持贤劫千佛(连载四)2 |
大慧宗杲禅师、玄奘菩萨后身,千古不易
(七)释惟护说:
大慧宗杲的气习不轻,他脾气刚直,性格开放,处事干练强势,曾烧毁他师父圆悟克勤祖师的《碧岩录》一百卷的刻版。从不示弱于人。爱好广泛,说法度众聚人力强,喜于参与政事,因此一生成为遭受政府排斥打压的对象。
[释惟护,《我的菩提路—从“正觉同修会”的旗手到“叛徒”》(卷三)]
释惟护又说:
玄奘大师习气轻微,他性格温顺,心性柔软,谦恭卑下,没有高慢心,慎言少言,法义辨正从不提人姓名,最重的一句话就是:“汝不解我意”。不喜交际。他一辈子只以经书打交道,埋头翻译经教工作。从不交一个朋友,他也不去度众说法。他从不参与政事,所以深受帝王的崇敬政府的支持。
[释惟护,《我的菩提路—从“正觉同修会”的旗手到“叛徒”》(卷三)]
事实:释惟护想要说明大慧禅师和玄奘菩萨不是同一人的前后身。然且不说此二圣是否同一位菩萨护持正法的前身后身,就释惟护之观点与史实而言却是大相迳庭。例如 玄奘菩萨如同大慧禅师“处事干练”,所以李世民两次督促玄奘菩萨还俗辅佐他处理国事;而当气愤到极点的士子郑尚明以默照禅来质问大慧禅师时,大慧禅师不愠不火开导,老婆到无以复加,此即如同 玄奘菩萨之“性格温顺,心性柔软”。又,克勤圜悟祖师吩咐 大慧禅师接任住持,然大慧禅师知道有人觊觎大位,在送行师父后,即舍寺自往后山另觅住处;此中唯见 大慧禅师“性格温顺,心性柔软”。
大慧禅师说“宁以此身代一切众生受地狱苦,终不以此口将佛法以为人情,瞎一切人眼”[《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5:“山野平昔有大誓愿:宁以此身代一切众生受地狱苦,终不以此口将佛法以为人情,瞎一切人眼。”《大正藏》册47,页919,下27-页920,上1。],玄奘菩萨亦是如此。当 玄奘菩萨与木叉毱多会面时,原本谦和,然等到木叉毱多出言藐视《瑜伽师地论》时,玄奘菩萨便转为“干练强势,从不示弱”,经由一场论辩,让贵为国师的木叉毱多从云端重重摔落到地上;从此木叉毱多见到 玄奘菩萨时都很恭敬而不敢再大剌剌坐著,甚至有时远远望见 玄奘菩萨就回避不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法师报曰:‘此有《瑜伽论》不?’毱多曰:‘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法师初深敬之,及闻此言,视之犹土。……法师即引《俱舍》初文问,发端即谬,因更穷之,色遂变动……毱多极惭……相见不复踞坐,或立或避。私谓人曰:‘此支那僧非易詶对。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出也。’其畏叹如是。”《大正藏》册50,页226,下22-页227,上10。]这让木叉毱多惊畏叹服万分的 玄奘菩萨,与释惟护叙述大慧宗杲的(于法上)“从不示弱于人”,到底差别在哪里?
对同是那烂陀寺讲师的师子光,玄奘菩萨先好言劝诫勿谤圣教,见其不从,便公开造论严厉破斥,令他颜面尽失黯然离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4:“法师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乃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师子光惭赧,遂出往菩提寺,别命东印度一同学名旃陀罗僧诃来相论难,冀解前耻。其人既至,惮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师声誉益甚。”《大正藏》册50,页244,下8-14。]这样用词犀利的 玄奘菩萨会是释惟护定义(不与人辩法)的“性格温顺,心性柔软”?师子光后来找了友人来帮他助拳,然这人只是远远地看见 玄奘菩萨威仪中显示出的威德力,便惊恐到不敢造次,准备好的话都生吞回去;如是威仪厚重的 玄奘菩萨会是释惟护说不去度众说法(不与人辩法)的“性格温顺,心性柔软”?
对于造恶论(《破大乘论》)主张“大乘非佛说”的般若毱多,玄奘菩萨以《破恶见论》回应,逐一破其恶见,此破斥之犀利让般若毱多惊恐万分,于是三次托词婉谢戒日王邀请他去曲女城大会,最后被逼到抛下老脸,遥向 玄奘菩萨方所赞叹以表臣服;[《成唯识论述记》卷4:“后,戒日王三度往唤般若毱多,欲令共我大师论议。〔般若毱多〕辞不肯来,一度辞不能乘马,一度辞舆热,复将母象往迎,即辞年老,遥叹大师,深生敬伏。”《大正藏》册43,页351,中3-6。]恐惧到这种地步,玄奘菩萨给他的印象哪是不去度众说法(不与人辩法)“性格温顺,心性柔软”的人?
更有同寺之谊的慧天法师,于曲女城无遮法会上,玄奘菩萨不假辞色,破斥他到狼狈不堪,无有世间情谊可说。这被破斥之惨烈,让慧天法师记忆犹新,后来书信到中国时仍提及此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夏五月乙卯,中印度国摩诃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书于法师。……慧天于小乘十八部该综明练,匠诱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师游西域日常共切磋。彼虽半教有功,然未措心于《方等》,为其执守偏见,法师恒诋诃。曲女城法集之时,又深折挫,彼亦媿伏。”《大正藏》册50,页261,上26-中6。]此中哪有释惟护说的 玄奘菩萨不去度众说法(不与人辩法)而“性格温顺,心性柔软”?
玄奘菩萨论及佛法正义,皆大剌剌举示对方名字,“逼走”师子光、“吓退”般若毱多,《成唯识论》本来也具名公布诸师错见,后因弟子窥基一再劝说,才改用“有义”,非是本意,何曾“法义辨正从不提人姓名”?如上所说,这“性格温顺,心性柔软”与“干练强势,从不示弱”是同时并存的。在《华严经》说菩萨摩诃萨习气,其中有“善根习气”及“教化众生习气”,因善根习气,则心性、性格温良淳善超乎大众;因教化众生习气,便能廉顽立懦,勇猛护持正法。
玄奘菩萨在译院中,每天一百多位弟子将侧边厢房都排队占满以求向 玄奘师父问道,同于 大慧禅师“说法度众聚人力强”。玄奘菩萨不喜政事,专务翻译;大慧禅师也不愿参与政事,然须与京师大官来往,亦摄受他们以利佛法发展,此则同于 玄奘菩萨须与皇上李世民来往一般。余者更无须解释。由此可知,释惟护之判断与史实有非常大的落差,纯属自己的臆度妄想。反而若就同是破斥诸方不假辞色而言,不免视 大慧宗杲禅师为 玄奘菩萨后身,皆是直接破斥误导众生之诸方大师,不假辞色,以分别义理论议殊胜故;若然,真千古不改其色,亦将直至末法灭尽。
理则顿悟,事则渐修,圣位菩萨示现于此间为三地心
(八)释惟护说:
但是大慧宗杲禅师末后临终,应该回兜率天才对,而大慧宗杲禅师一生都并没有任何净土修行的表现,何况是兜率天弥勒净土?!
[释惟护,《我的菩提路—从“正觉同修会”的旗手到“叛徒”》(卷三)] 释惟护说:
如果萧老师是“玄奘大师”的转世,应该开悟之后,顿至“三地”或“三地”以上才对。为什么还只能一步步的递进呢?
又说:
难道“三地菩萨”—玄奘大师退失了“三地菩萨”境界,需要重头再来?
[释惟护,《我的菩提路—从“正觉同修会”的旗手到“叛徒”》(卷三)]
事实:释惟护之论议是要说明 玄奘菩萨与 大慧宗杲禅师是不同的人,以说 平实导师也是不同人。在此且不说这三位圣者是否为同一位菩萨的前身后身护持正法,但依佛法说:玄奘菩萨、大慧禅师、平实导师皆是有初禅以上证量的圣位菩萨,都可上生色界天,并非只能于欲界天或人间受生。当圣位菩萨舍寿后中阴身现起时,世尊便为指示,若人间尚有任务就去投胎,非必回兜率陀天;又圣位菩萨禅定证量高者(四禅以上)则可至色究竟天,但一切皆依如来指示为前导,听命法王尊。又,圣位菩萨示现于人间之证量,是否分身现起,为几地之证量,种种世间事情之示现处,亦非大众可知。
理则顿悟,事则渐修;未离胎昧之菩萨再来时,并非证悟后,过去生所学所证就一时全部回复。佛说众生无始以来都曾证得四禅、五神通,然有胎昧的菩萨悟后犹然无法发起。又如 玄奘菩萨示现年少证悟后,仍须寻找到《瑜伽师地论》(根本论),才慢慢回复往昔之圣位智慧证量;但却不是如初悟之七住菩萨还要继续历经一大阿僧祇劫之修学方才完成,而是在每一生之十年左右即可完成(回复往世证量)。玄奘如是,沩山灵佑如是,大慧宗杲如是,平实导师亦复如是,方能将从凡夫位修至三地满心的种种现观境界为大众宣说之,岂是偶然!然圣位菩萨之真实证量难知,于世间大都示现布施、持戒圆满,而三地满心位具足之四禅八定与五神通,则非三贤位学人迫切必修之处,故圣位菩萨住持世间正法时,往往示现为三地住地心乃至初地心境界,不作更高层次之示现(除非有特殊因缘),否则众生何由亲近?
当知《楞严经》所说“真菩萨、真阿罗汉(指阿罗汉菩萨)”主要以论及脱离(分段)生死、生死自在为准则,此等大乘菩萨皆不自称是已断分段生死之菩萨再来(指别教七地满心以上菩萨或通教阿罗汉菩萨)。揆诸史实,玄奘菩萨、大慧宗杲禅师皆未示现断除胎昧及断分段生死,而无妨是地后菩萨。又,玄奘菩萨、大慧禅师勇于护持正法,后身必现此末法人间,再为法主亦是常事。《楞严经》说证悟菩萨(纯想非情,兼有福慧、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心开”即是证悟),一切净土随愿往生,[《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8:“纯想即飞必生天上,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及与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大正藏》册19,页143,中16-18。]本无障碍;而兜率天宫本为净土所摄,见道者自可随愿上生;然证量极高的圣位菩萨虽有行愿,来去亦依如来法王尊作主。末法万年后,届时于兜率陀天宫内院依证量坐定时,便知 玄奘菩萨、大慧禅师、平实导师之真实证量以及是否为同一人[平实导师曾说,舍寿时自当说明来历。]。
|
|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