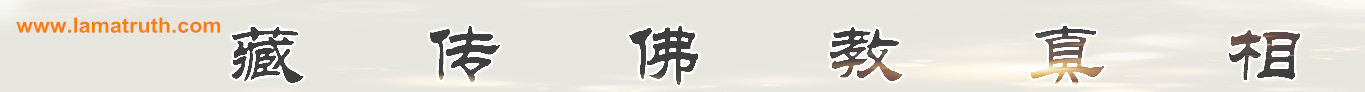| 首页 » » 破斥琅琊阁 |
空谷跫音——护持贤劫千佛 (连载二)3 |
正確解讀《成唯識論》,唯地上聖位菩薩可致之
(五)琅琊閣寫手質疑:【蕭平實居士為什麼如此解讀《成唯識論》?蕭導師扭曲《成論》很明顯為的是一個目的:將他所謂的「明心開悟」抬高到「見道位」,同時又把明心開悟的條件(禪定)和斷煩惱的功效拉低。】 又說:【抬高,是為了讓大家覺得自己辛苦付出得來的「密意」是值得的。「見道位」是不退轉位,永離三惡道,在大乘佛法裡面是一個很殊勝的階位,是凡夫與聖者的界限所在。】19
辨正:琅琊閣寫手認為平實導師將明心開悟「抬高」到見道位,這是因為琅琊閣不接受明心是見道。然玄奘菩薩已在《成唯識論》說,「見道位」含攝「真見道」、「相見道」及「見道通達位」,明心即是真見道;琅琊閣寫手卻認定見道是(或幾近)入地的聖位,不只是不退轉住。窺基菩薩雖誤判真見道與相見道階位,但猶舉出《菩薩瓔珞本業經》七住不退轉住20,合於《華嚴經》所說,即凡夫、聖位之間另有已悟賢位菩薩。當琅琊閣寫手說見道位「在大乘佛法裡面是一個很殊勝的階位,是凡夫與聖者的界限所在」時,則已悟之賢位該屬凡夫還是聖位?顯然理路不通。而窺基說相見道要修學很久,琅琊閣寫手卻仍掙扎地將見道位變成幾近或等於聖位專屬。包括經王《大方廣佛華嚴經》在內的至教量皆說有已悟賢位不同凡夫,《華嚴經》、《楞嚴經》等等經論皆說聖位前有三賢之三十位次: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非僅信位凡夫及聖位,亦即賢位含攝有初住至六住之資糧位,以及七住位(不退轉住,即見道明心)至十迴向之真、相見道位。所以真正提高這明心見道位階的人是誰?是一口氣認定見道就是聖位菩薩,又同時否定禪宗明心是見道,如是為琅琊閣寫手奇特的主張。至於明心見道所須的定力條件是具未到地定,非必於初禪或四禪等禪定著眼,如彌勒菩薩所說;而琅琊閣寫手卻違聖教而將之直接提高到必須第四禪具足,將三地滿心位菩薩須滿足的修學內涵也納進來,變成了一個高不可攀的見道。
古來禪師本不喜理會世智辯聰之人(例如現代學術人、古時的儒家學人等)的意見。明心開悟本是見道,否則經中說的「般若波羅蜜多正觀現在前」又是什麼?大乘禪門中真悟祖師從來少有精讀藏經者,悟前悟後大都如此。德山禪師說:「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21大乘法尚非二乘聖僧境界,何況學術凡夫?然平實導師宅心仁厚,總留生路與人。退轉者以為學術人世智聰辯能造論文,甚為稀特;豈不知真悟者縱使不會學術論文、格式等樣樣不通,然一平議的短文就足令世智辯聰者從此名聲掃地。六祖惠能得祖衣時仍不識字,遑論寫作;千年後,廣欽老和尚證悟時也不識字,更別說寫論文;然兩位大德說的話可流傳後世,而琅琊閣寫手說的世智聰辯之學術人,則個個汩沒於生死大海(除非求生極樂)。若受平實導師提拔的正覺悟者是「小學生」,博士則是等覺菩薩,皆非紙上學問之世智聰辯學術人可比;大乘法是實證,當向親證者學。 琅琊閣寫手認為其說即是玄奘菩薩的真義,然如前說,其大要觀點已先予簡單四點回覆,顯然琅琊閣寫手自說非真。琅琊閣卻又在是否他該註釋《成唯識論》的問題上回覆過,他說註釋《成論》的「這些學者大師對《成論》的考證已經頗為詳盡」22 ,他以為《成唯識論》由世智辯聰的學術人依文解義來立論已足成辦真義,這也可能是他認定玄奘菩薩真義的來源。在此針對琅琊閣所說:第一、有人註釋,且「不能盡錄」(所有註釋)。然此純是虛語,琅琊閣大可盡錄無妨,可讓人見識是哪一位現代修行人真正註釋過《成唯識論》。 第二、這些註釋的考據「頗為詳盡」。此猶然虛語,學術人堆砌文字之考證與真義有何關聯?世智辯聰者往往認為其所思議即為佛法,悍然拒絕信受如來說大乘法不可思議。所謂「考證已經頗為詳盡」只能證明琅琊閣個人刻意模糊焦點,因為正確的註釋本身非僅考證,更須證義方得無誤;這也同時表達了琅琊閣認為這些學者的註釋無誤,然于淩波、韓廷傑、釋演培對第一義的立場有偏差,琅琊閣可能因同屬學術同好會,故難以檢擇對錯。(平實導師叮嚀,從來不要特別說誰沒有開悟,說錯的人,只要他不說自己開悟,也不要評論。然由於琅琊閣不肯老實回覆能否註釋《成唯識論》,卻拖人下水,連累這些人在此受評議,實非此處寫作之本意。)如果琅琊閣轉說這些註釋本自有誤,則不該著文舉說貽誤學人。且琅琊閣自認解讀《成唯識論》超勝平實導師,又沒有人作出正確的註釋,如何自說(要他)「注釋《成唯識論》完全不必」?任何人皆能斷言這說法避重就輕,「猶是虛語」。若琅琊閣強辯註釋無誤,自是無理;真悟者尚不忍卒讀,何況平實導師。 若未證如來藏者可以依文解義而註釋正確,實證如來藏且有道種智的平實導師反而不懂《成唯識論》而不應註釋,這種道理任誰也說不通,有智之人豈能信之乎?
入海算沙徒自困,聖位示現有誰知
琅琊閣之桀驁不馴、孤傲不群,不受善知識教,只能說這是他學佛必經的歧路尚未走完,必然辛苦放棄平實導師令他一次看清佛法全貌總相的正觀〔編案:般若總相智〕,又回歸到世智辯聰學術人之各種分類解析研究的觀點。在他眼中,世間凡夫寫的「專業佛學書籍和論文」是「博士論文」,正覺證悟學子有如「小學生」23。無怪乎如來一再告誡佛子:大乘佛法不當對淺學說,以大乘法聞思修證非世智辯聰之學術人可至故。學術界最出名的就是釋印順,然這位偽佛法專家寫的從來不是「專業佛學書籍」,若有人跟隨釋印順觀點所造的自然也非「專業佛學論文」,充其量亦只為「外道見之文」,因為釋印順四十二冊書中所說全都言不及義。 諸佛菩薩並沒有虧待琅琊閣在人生上所遇到之法緣,讓他知道學術世智辯聰的釋印順,也讓他知道有位不世出的平實導師。如今琅琊閣已將「正覺觀點」拋棄了,也找到了同好,都是在將一個又一個的名相予以重新拆解,抱著學術考據入海算沙的精神,字字窮究,在名相大海中尋找最適合的名相解釋24,然後自困於釋印順的學術觀點中卻儼然自得。他們生命中實際無須明心開悟,他們此時也不應求悟,見道距離對他們來說太過遙遠,顯然見道所需的條件都付之闕如故,無怪乎轉依不能成功,當然無有悟之功德。 當大眾遠望著賢聖背後身影,生起景仰賢聖之心時,這些學術同好者、世智辯聰之人,卻以全然不同的用心來追求堆砌於佛法名相最極精確的解釋,所唯一依靠的是經論上的文句用字遣詞,也以此評價聖賢;這就是世智聰辯之人所熱愛的事情,認為這才是令世間有著次序條理之道。 中國禪師則施展著大相逕庭的霹靂手段,完全不具學術考據精神色彩:凡有學子請問,禪師們往往就賞上一掄棍棒、打將出去;證悟祖師也幾乎很少閱讀經論,惠能更是不認識字,咱們佛法禪宗這一切一定是在琅琊閣精確的世間次序之外,沒有安置之處,琅琊閣不會接受禪宗證悟的標的與禪師的風格—義理海吞天下,行事睥睨諸方(猶如獨斷專行),且在公案後的諸真悟禪師一再利斧斬斫的犀利評論中,琅琊閣如何忍受得了?自是過去生唯憑真悟禪師放手,從無絲毫能力得入此甚深第一義中。因為禪宗萬法歸一的親證,破壞了他精心計算海沙的美夢,禪師無所畏懼的錘鍊風格在其心中,應該成為了橫衝直撞,嚴重衝突了他在生命中所設定的理想次序。 如今琅琊閣寫手捨棄了師父平實導師的教導,可能他的眷屬會覺得很可惜,然實際並不可惜,因為他疑根種子勢力如此強盛,早些爆發成現行並無不好。這一生他值遇了論議超勝世間的平實導師,人生已無遺憾。師父讓他此世受到正法完整的對外道邪謬之破斥(包括對六識論等外道邪說的破斥)與正理之熏習,即使他接下來還是選擇這迂迴的道路,然對其而言,這卻是他最快成佛的捷徑,沒有這樣必經的痛楚,他心中將永遠狐疑,將來無法走在正確無誤的道路上。此世他真的很幸福,由於平實導師殊勝威德的攝受介入,讓這事走向了對的方向,一切當如是觀,他的眷屬因此無須遺憾。 當琅琊閣生起任何對師父不屑、不敬、不滿的心行時,師父平實導師沒有跟他計較,一樣繼續示現演出這預定的人間度化戲碼,將此五濁惡世橫逆轉為佛事,在似乎沒有琅琊閣所關心的異能中,來攝受眾生。當這些學問學術人、世間知識人在文字堆砌世界中,只關心其所想的境界是最值得被推崇時,等到現象界突然出現了他們無法否定與解釋的現象,他們在驚嚇愕然後,才會因此困惑,乃至懾服,因為自己的所見、所思、所喜被徹底推翻了,所以他們是應該被神通異能所度的俗人,從來不是佛法智慧要度的真正學人。(待續)
|
| 首页 |